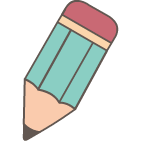關(guān)于木耳冬菇瘦肉湯是個什么梗?
人類一直生活在誤解中。人與人的誤解,,族群與族群的誤解,大至國家與政治之間的誤解,,彼此都自以為是,此乃世界范圍內(nèi)的常識,,即便最親密的人,,也概莫能外。遺憾的是,,大多數(shù)的文學觀卻認同并鼓吹人心的互通,,把理想國的幻境當作現(xiàn)實的準則與律條。然而,,事物的法則與此相反,,人心可能溝通,,卻無法達至完全,,道德與法律由此而生。文學無法回避這一法則,,努力修補和完善這一法則,,以期抵達彼岸。真正的文學,,始終圍繞這一法則,,憂慮徘徊。
在徐肖楠的小說《秘畫之戀》中,,我讀出了這樣的憂慮,。紅角楊和秘畫,這些行將消失的東西,,如此糾結(jié)于心,,它們在小說每個人物的精神生活中,占據(jù)了大面積的領(lǐng)地。幾乎所有的人,,都為此傷懷,。不是單純的睹物思人式的懷舊,而是因此失落了自己,,破壞了想象中的自己,。這是一種更為闊大的人類自虐,我相信這種自虐,,是人類文明很難規(guī)避的弊端,。
不管他們是否在現(xiàn)場,只要提起紅角楊,、秘畫,,一連串的歷史和故事,潺流而至,。他們跟隨潺流,,將所有未來的憧憬,都壓縮在對紅角楊和秘畫的傷懷中,。我強調(diào)了傷懷與懷舊的差別,。這是徐肖楠,作為評論家的小說家,,對“自己的小說”的預(yù)謀,,他以感性的觸角方式,把評論家的理性思維,,嚴密地潛伏在人物的情緒線路上,,形成一種邏輯的圖寫。這些有閱歷,、有情感傷痕的小布爾喬亞們,,在當下的讀者面前,顯得文弱,,顯得雅致,,顯得感傷,而且缺少當下時代的嘈雜詭異,。他們把不合時宜的教養(yǎng)寫在臉上,,有一種拽回消失時代的柔韌……于是,徐肖楠成功地畫出了一群人的失樂園,。
肖楠的克制是平常的,,而肖楠的激動是突發(fā)的。他在“自己的小說”里,,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自由,。他終于可以在平常的克制和突發(fā)的激動中,,沖突同時圓融了他的矛盾。沒有這部小說的誕生,,真實的肖楠,,無從表達和訴說。
自從聽說肖楠要寫小說,,我便明白,,這是肖楠終于尋找到的自我解放。以他的評論,,他不但無法與自己和解,,也難以和文學,乃至文字達至共和,。而小說讓他暫時掙脫了理論批評的冬烘,,得以有勇氣面對內(nèi)心的沖動。我本以為肖楠會借此形式表達抱怨,,借小說詛咒生存的不幸部分,。但沒有。人物平緩的出場,,意想不到的沖突,,融化在輕曼的情緒循環(huán)中,愛情留下漫天的遺憾,,卻不曾仇恨,,不曾不共戴天。
只有謙謙君子,,才能在懷舊的生存中,,以各自的認知,達至一種共同的抒情,。紅角楊的抒情,,有些陰鷙的抒情,它們躲藏在充足理由的唱響中,,紅角楊與秘畫的唱響中,。肖楠在這種看似個別,、身份不同卻又相似閱歷的抒情中,,努力區(qū)別各自的認知、性格,,以及性別經(jīng)驗的不同,。比如唐岱,“紅角楊園深藏的命運在等待他,,讓他來發(fā)現(xiàn)還是讓他來觸動,,是神話之手還是現(xiàn)實之手,?”比如唐岱曾經(jīng)的戀人、今日他人的妻子桑梓,,“玫瑰還在手上”,,可“韶華已逝,還想重新依在他身邊,,和他一起與紅角楊這個神話園同在,,與那些草木星光和飄蕩的女神同在”。
小說里的布爾喬亞們,,個個都是哲人,,都喜歡沿著泰戈爾的靈魂路線:“世界以痛吻我,我卻報之以歌,�,!弊杂X地投入紅角楊園的傷懷與捍衛(wèi)、秘畫的尋找中,。這是那一代人的集體情結(jié):傷懷一個年代的消失,,尋找不曾見過的藍圖。
再一次相信,,小說的理論家才能真正寫好小說,,不是出于職業(yè),而是因為修養(yǎng),。小說不是生活本身,,而是邏輯生活,即生活的邏輯化,。它寫的是生活的目光,,只有這目光,才能看到靈魂的戰(zhàn)栗和波動,。小說,,就是自己和自己、和世界的對話,,與一群名字叫“自己”的人的對話,。肖楠換了一種方式,寫出了不一樣的小說,,自己的小說,。魯迅曾主張:信馬由韁,寫去,,是什么就是什么,!這才是寫小說的氣度。